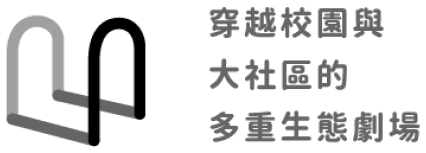多元族群的重組、衝突與融合
張琬琳
建中學生名列暴亂案件人犯名冊 by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戰後的政治情勢,使兩岸人民皆無可遁逃地經歷了大時代的劇變,不論是外省人面臨骨肉相隔、流離失所的國仇家恨;或是本省人的認同困頓與迷惘、在語言和文化的錯位中拼湊支離破碎的國族想像。
1949年,國民政府在在國共內戰中連連失利,加以中國大陸幾經烽火摧殘,民生凋敝,數百萬軍民流亡的逃難潮,一路由華北竄向南方,最後在驚惶與恐慌之中,來到了臺灣。而隨政府撤退臺灣的大量軍民湧入臺灣後,作為臨時首都的臺北,開始面臨真正嚴峻的文化衝擊與空間考驗。
由於日治時期,殖民政府即刻意將臺灣人與日本人的活動範圍區隔開來,因而當日本人戰敗被迫遷離之後,原本以居住日本人為主的臺北城內、城南地區,皆留下了空缺,戰敗的日本人毫無選擇,除了少數專技人員之外,其餘百姓皆必須在短暫時間內,變賣在臺灣經營的所有財產與土地,接受遣返回國。因而在戰後日人產權尚未妥善處置之前,在城中、城南一帶「佔房子」、「剝狗皮」的情景四處可見,鍾肇政即在其回憶錄中,談到戰後初期日本人急於脫產、「剝狗皮」的情形,[1] 丘秀芷也書寫了當年情景:
- 那些房子,「先住先贏」……一光復日本人多數走了,誰先住進去,誰就有居住權!空房子到處都是。[2]
- 日人一走,一時產權「真空」。有的有房契,日本人急於脫售,據說以一棟房子房契換一隻鵝、一隻雞都行。他們要走,搬不了那麼多東西走,於是在路邊典賣東西,換一點點錢或一點食物也好。戰後物資,尤其糧食奇缺。房子,這時變成沒有用了。
- 日本人較矮,臺人稱他們為「四腳狗」,日據時剝削臺人的不在少數,這一下子局勢轉換,他們不得不變賣東西,臺人笑是「剝下狗皮」。[3]
原本終戰之初,日本人留下的大片空間,成為戰後首批遷入人士足可利用的最佳選擇,因而在1949年國民黨淪陷大陸之前,不論是奉命接收臺灣的公務專技人員,或是自行遷臺謀生的外省人士,皆能擁有較佳的居住空間,例如青田街一帶的臺大教員宿舍,多配給當時接收臺大的第一批教職員所使用。[4]
然而隨著國民黨在中國大陸局勢逐漸危急,外省人陸續遷臺者增加,這些從日產接收來的公家宿舍逐漸不敷需求,加以日產的接收、清點以及分配,對於在內戰之中奉命接收臺灣的陳儀政府而言是一大考驗,許多公、私有財產接收過程之中,爭議不斷,[5] 而人心不安所致之社會震盪,使物價飆漲、通貨膨脹加劇,在兵馬倥傯、青黃不接的局勢之中,眾多攜家帶眷的百姓等不著落腳之處,索性就地佔用個空房子,若沒有空屋就找個空地,隨意搭起簡陋的房子克難地居住。
由於民間存在著迫切的空間需求,不少受國民政府延攬赴臺的公教菁英人士,初到臺灣卻無落腳之處,因而暫時居住於其他友人家中,例如在城南,錢思亮曾住在南門口福州街的臺大傅斯年校長宿舍、趙元任先生也曾借住錢思亮先生家中、後來胡適之先生和梅月涵先生也曾同住於此;齊邦媛來臺大任教之初,也借住在青田街的馬廷英教授家中。[6] 即使是被聘來臺的教授,學校有時也未能安排住處,如何安排這些外省知識份子們的居住,成為一大問題。
許多個別來臺的民眾透過個人的關係尋找住屋,不少機關也為其員工居住的問題大傷腦筋,各機關之間也展開彼此借空間、搶宿舍的情形,例如中研院史語所、故宮博物院向臺大借宿舍、1949年的《民族報》上,也刊載〈婦女工作會自顧不暇,沒有空宿舍容納別人〉的報導,以婉拒其他單位覬覦其原本擁有的三十間宿舍。[7] 不論民間或公家單位,民眾住的問題總是不斷滋生,因而「先搶先贏」、「先佔先有」的情形。
戰後臺北人口遽增,並且以令人無法預料的速度不斷擴張,空間不足的問題、糧食不足的問題,以及通貨膨脹的問題,又連帶著地價、房價與房租的飆漲,接連地發生。羅蘭也回憶當時的情形:
- 旁觀逃亡潮,也旁觀那光復後第一波的房價飆漲,日式房屋以每疊「他他米」一兩黃金算。[8]
由於人口密集、許多百姓居住空間及衛生品質不佳,加以物價及房價飆漲所衍生之貧富差距、資源分配不均等狀況,致使經常有各類社會案件在臺北發生,這和臺北在日治時代民風純樸、夜不閉戶治安良好的情況差異極大,但日久之後,人們也於是漸漸習慣臺北小偷猖獗的治安。
- 臺北小偷之猖獗,臺北人雖然自己未被偷,一定也聽過親友被偷,遭偷在今日可說是家常事。[9]
- 那年頭很多人丟小東西,衣服鞋襪都有人偷,連木屐都有小偷偷。更大膽的「大偷」是偷電線桿上的電線、地裡的自來水管,因為電線中有銅線,水管鉛做的,在那物資奇缺的時代,值錢得很。……[10]
戰後初期的臺灣社會,百廢待興,儘管同時臺灣內部對於陳儀政府的軍政統治開始異議不斷,且臺灣文化界亦對於政府貪敗施政展開嚴厲撻伐,[11] 但在多數自願來臺服務的外省人士,大多對臺灣存著較佳的印象,本省人亦對這些外省人士誠懇尊敬且溫和有禮。[12]
然而儘管如此,當時社會與經濟環境的巨變,使得族群和階層的衝突加劇,在許多文學作品和居民的口述歷史回憶中,可看到當時城南在政權轉換之際,所遭逢的族群撕裂和意識形態對峙的狀況。文化的衝突、殖民位階未見轉變(再殖民)、文官任用制度與政治歧視、這些都是促成文化對峙的種種原因,另一方面,日本人離開後,來「填補」日本人經濟殖民統治者職位的,僅有非常有限的少數是本省臺灣人,而多數依舊是外省人的職位。這情況在城南尤其顯而易見,城南的殖民產業經濟、文教生活圈,延續了日本時代的規劃脈絡,在戰後更呈顯了族群位階的不平等,這也是導致日後族群衝突、國民政府對反抗者執行鎮壓大屠殺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許多城南老一輩居民的歷史回憶裡,更印證了這些大歷史的觀點。二二八事件前後,城南籠罩在肅穆的而恐怖的氛圍裡,族群血腥對峙事件爆發後,城南的居民如驚弓之鳥,家戶緊閉門窗,不敢出門,接連在南門口公賣局的抗爭事件、在植物園刑場的屠殺,這些都血淋淋在城南場域裡發生。
客家耆老溫送珍回憶當時臺灣經濟混亂,他在南昌路所開店經營的「大源百貨行」被國民政府軍持槍掃射,店內貨品被洗劫一空;老居民李女士回憶,當年還幼小的她,被父母要求萬萬不可出門,她在南昌路二樓的自家陽臺柵門的縫隙裡,親眼看見路上一輛接一輛的軍用卡車上,滿載著手腳被反綁的民眾,一旁還有穿著制服的士兵,手持機槍,強押著即將被處死的民眾,當街遊行示眾……
然而,即使再如何混亂無序的時代,生活總是要真實地走下去,城南的知識份子們,在逐漸覺知到政府一路高唱的反攻大陸、復興中華的國族願望,已愈行愈遠而難以實現之時,開始俯視自身當前所在、此一最真實而存在的空間時,才驚覺到也對它產生濃厚的情感,只是從前總不認為異域可以為家,在暫時居所裡,累積了數十年、甚至已孕育新一代又一代的空間認同之後,這一座滿載著作家生命中大半輩子記憶的城,已不再是陌生的海隅之都,它承載了眾多外省知識份子在臺灣大半生的記憶,而在臺北城南所居住的日式宿舍,索性就這麼居住下去吧!只是「不再歇腳就是了」,這裡原來也是「家」,一個累積大半精采人生的地方。
[1] 鐘肇政,《鍾肇政回憶錄》,(臺北:前衛),1998。
[2] 丘秀芷,〈三線路〉,收入《回到中山堂》(臺北:文化局,2002年,頁129)
[3] 丘秀芷,〈二二八事件前前後後〉,收入中國婦女寫作協會主編,《我們的八十年》1991,時報出版社,頁197。
[4] 左祥駒,《古蹟保存作為一種空間的社會生產 : 臺北市靑田街的日式宿舍保存運動》臺大城鄉所碩士論文,2006。
[5] 例如有利可圖的事業或財產,往往未經呈准即擅行接收、變賣或挪用等等。參見何鳳嬌,《戰後初期臺灣土地的接收與處理1945-1952》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年,頁98-104。
[6] 齊邦媛,《巨流河》,(臺北:天下文化),2009年,頁290-293。
[7] 文見《民族報》,1949年5月27日第二版。
[8] 羅蘭,〈幾頁民族滄桑史──是誰奮鬥誰犧牲〉,《歷史月刊》24期,1990年1月,頁16。
[9] 陳克環《書癮,書緣》(九歌,1980年),頁99。
[10] 畢璞,〈危樓歲月〉(中國婦女寫作協會主編,《我們的八十年》,時報,1991,頁200。
[11] 臺灣文化界對於陳儀政府對於本省人的政治歧視、指控臺人奴化,並擅用軍權審判臺灣人等作為極為不滿,加以政府在接收日產的過程中,貪腐霸道且積弊無能,因而展開各項文化行動,並對於現政加以撻伐。相關論述及史料研究,可參考陳翠蓮,〈戰後初期臺灣人的祖國體驗與認同轉變〉,收入《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臺北:遠流),2008,頁333-386。
[12] 林桶法,《一九四九大撤退》(臺北:聯經)2009年,頁363-373。

【專論】居食城南:多元族群與多重歷史脈源的常民生活空間
臺北自清代以來的市街發展模式,即高度仰賴經濟基礎,區域的發展因商業活動的充裕,漸漸累積多元的人文活動風貌。從大臺北市街發展的脈絡來看,城南的拓墾與市街規劃,都與臺北都市幅員的擴張、居民族群多元的特色…

動盪時代的城南安居:外省族群流遷台灣的歇腳之地
戰後外省籍人士的遷徙,是一個漫長、輾轉而艱辛困頓的歷史過程。日本戰敗後,在台灣留下的房舍、事業及物品,原則上需依「臺灣省接收日人財產處理準則」接收,並由日產處理委員會統籌處理,進行轉撥各機關,或辦理標售…

多元族群的重組、衝突與融合
戰後的政治情勢,使兩岸人民皆無可遁逃地經歷了大時代的劇變,不論是外省人面臨骨肉相隔、流離失所的國仇家恨;或是本省人的認同困頓與迷惘、在語言和文化的錯位中拼湊支離破碎的國族想像…

城南的商業飲食文化與族群變遷
日治時期,由於領臺初期官吏士兵紛傳水土不服,使得總督很快的便注意到臺北蔬菜產量的匱乏,因而建立了種植日本蔬菜的獎勵制度,並總督府在南門外購地設置苗圃。城南一帶或因尚未開墾的田地甚廣,由少數住戶嘗試種植…

城南客:多元族群與信仰
城南的南昌路,日治時期即是兒玉町的主要街道,沿街商店林立,有自行車店、料理店、洋果子店、書店、洗衣店、理髮店、百貨行、碾米廠、木材行、雜貨店等,是城南經濟活動聚集的中心。商店主要由日本人經營,店家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