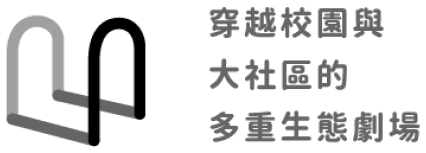動盪時代的城南安居:外省族群流遷台灣的歇腳之地
張琬琳
by eshensh
戰後外省籍人士的遷徙,是一個漫長、輾轉而艱辛困頓的歷史過程。日本戰敗後,在臺灣留下的房舍、事業及物品,原則上需依「臺灣省接收日人財產處理準則」接收,並由日產處理委員會統籌處理,進行轉撥各機關,或辦理標售、租用、接管等事宜。[1] 因而城南地區的高級日式房舍,亦隨著日產分配各項作業的進行,被分配到公教眷舍的公務員及教員,才著手紛紛自其他地區遷居至本地,進而落腳於此。
例如任職於「國語推行委員會」,亦擔任「國語日報社」編輯的何凡與林海音夫婦倆,就在一間小小的日式房子裡,開啟了大半生的文化事業。林海音寫一家三口在榻榻米上生活的日子:
- 三十八年初,我們就搬到重慶南路三段的宿舍來住,十八坪不大,祇有一頂日本「皇軍」色的大蚊帳,一張矮桌,也就勉強可以應付我們一家人二十四小時的生活所需了。三個孩子──八歲的,四歲的,兩歲的──就每天在這十八蓆上翻來滾去。榻榻米的房子,日子倒也好混![2]
和林海音一樣,何凡亦在小房子裡平凡地生活:白天工作,晚上一邊照顧家庭,一邊在書房兼臥室的「三疊室」[3] 裡,伏首「玻璃墊上」[4] 勤奮寫作,一字一字,爬了大半生的格子:
- 那時我們住在臺北重慶南路三段的宿舍裡,我有一間三疊室書房,海音則在長廊的窗戶邊上擺上一張書桌,我們全家六口住在十四疊半的榻榻米上。我和海音白天上班,晚上熬夜寫稿,兩人同心協力照顧家,家庭生活愉快,寫作力旺盛。[5]
林海音跟隨在國語日報社工作的夫婿何凡,在戰後搬遷至重慶南路三段的國語日報員工宿舍,然而從他們的作品中,可發現當時的屋內空間,已不似日治時期日本人規劃城南高級住宅區的理想樣貌,反而是狹小、侷促、混雜、拼貼的違建式日本建築:
- 我們住在臺北城南一間不到三十坪的日本式榻榻米房子裡……日本房子玄關入口改成臥室,小院子裡貼近街門的牆邊又搭建了一間像傳達室般的臥房。[6]
日本時代留下來的日式屋舍,經過二戰戰火的摧擾,以及戰後混亂膠著的大規模人口遷徙與都市變遷,加上戰後國民政府對於日宅的分配,有時是以一屋多戶的方式,依照公職位階予以配給,因而每戶家庭實際的生活空間仍顯侷促。由於眾多家庭侷處於窄小的日式房舍裡,空間不足,而日式建築多為木製建材,隔音效果不佳,難免互受干擾,因而住民們開始在格局上加以改建、隔間,或經常在原建築之外增設違建,以及改闢出自家獨立的出入口。[7]
然而並非每戶人家都被分配到如此狹小的日式宿舍裡,住在廈門街113巷8號的余光中家,因父親余超英曾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教育及僑務要職的緣故,而配有一棟佔地一百多坪的日式房子,[8] 正在臺大外文系求學的余光中,於是和母親倆,從1952年住進這棟偌大的房子。此後,他「近半輩子在其中消磨,母親在其中謝世,四個女兒和十七本書在其中誕生」。[9] 余光中書寫他在廈門街的這間日式房子裡,與妻子(亦是余光中遠房表妹)范我存一同在此度過婚後安恬而穩定的生活,以及夫妻相互眷戀的濃厚情感:「三十五年前有一對紅燭/ 曾經照耀年輕的洞房/ ──且用這麼古典的名字/ 追念廈門街那間斗室/ 迄今仍然並排地燒著/仍然相互眷顧地照著」。[10]
戰後國民政府有計畫性地將龐大的公職體系人員,以及知識份子們的家庭眷屬們,適地適所地安頓於接管日產而來的各式屋舍中,而這樣安定民心的做法,是政府透過生活空間的支配,以掌握對公教階層穩定治理的途徑。這些外省籍人士們,在歷經中國戰亂與流離,並被迫離開原鄉親密社群之後,在島內孤立而斷裂的生命,已不容再支離破碎,加上人們對於「家屋/家」(house/home)的空間經驗特別強烈,家的安置,讓人們感到安穩與切實,一個「家」的經營,使人們開起對於外在各種空間的認識,以及串連出有個人的記憶、想像和夢想的地方。[11] 因而,「想要有個家」,是他們在顛沛流亡後,來到這陌生城市急切的需求與渴望。
戰後的國民政府,一方面藉由權力、經濟與文化支配的全面控制,以掌管人民接受統治者的道德、政治以及文化的價值觀念;另一方面則考量被行使對象的政治傾向,而更加強維護與之同時播遷來臺之眾多知識分子與中產階級的利益。
戰後的城南,在官方主導之下,接連幾個以主流國家意識形態所號召的「民間」文藝團體相繼成立於城南:1953年的「中國青年寫作協會」,呼籲全國與海外文藝青年「和我們站在一起,同心同德,為反共抗俄而寫作,為復國建國而磨礪」[12]、1955年成立的「臺灣省婦女寫作協會」,旨在結合自由中國的婦女們,從事自由和文化保衛戰鬥:「我們要發揚文化,我們要保護自由,所以我們結合在一起,努力以赴,不但要使自由燈塔下的婦女廣泛普遍的享受到自由與文化,並且要肩負衝破沒有自由與文化的鐵幕,拯救在黑暗中掙扎的姊妹們」。
另外,同樣具有官方文藝主導性質的「中華民國新詩協會」也設址於城南,這幾個官方主導的文藝團體,從文學到藝術、從軍人到百姓,乃至於各階層志士、青年到婦女,都備有組織緊密、系統嚴密的文化宣傳體制,因而幾乎囊納了全臺灣當時中文書寫作家群。[13]
透過國家機制的空間支配與家眷安置,在這經常只關注於大歷史、大時代之國族意識的環境中,這些具有智識能量的精英人士與科層官僚,獲得了一處暫時歇腳的庇蔭所;並且,時間隨著人們的鄉愁記憶緩緩流逝,於是乎人們開始環視、凝望自己多常年來於城南被安置的住所,而發現自己竟也對它產生濃濃的感情依附,於是,這個當年被政府政策性支配與安置地方,成了住民的意義中心和生命觀照的場域。
[1] 詳細日產接收資料,可參見薛月順,《臺灣省政府檔案史料彙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期》(臺北:國史館,1996)。
[2] 林海音,《剪影話文壇》(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84),頁4。
[3] 夏祖麗,〈從三疊室寫起──我的父親專欄作家何凡〉,收入《人間的感情:感人的真實故事》(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85),頁117。
[4] 「玻璃墊上」取自何凡從1953年到1970年,在聯合報副刊發表的專欄名稱。參見夏祖麗,〈從三疊室寫起──我的父親專欄作家何凡〉,收入《人間的感情:感人的真實故事》(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86),頁117~119。
[5] 何凡,《何其平凡:何凡散文》(臺北:三民,2002),頁109。
[6] 夏祖焯,〈虹橋機場〉,收入《從城南走來:林海音傳》(臺北:天下遠見,2000),頁198。夏祖焯,筆名夏烈,林海音的長子。
[7] 參見劉可強主持,《市定古蹟紀州庵修復調查研究委託技術服務案報告書》(臺北: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2005),未出版,頁3-17~3-19。本資料為臺大城鄉所受案於臺北市文化局,針對位於城南之市定古蹟紀州庵及其週邊環境進行調查研究之委託技術服務案之調查結果。
[8] 傅孟麗,《茱萸的孩子──余光中傳》(臺北:天下遠見,1999),頁50。
[9] 余光中,〈思臺北.念臺北〉,《青青邊愁》(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80),頁131。
[10] 余光中,〈三生石〉,《五行無阻》(臺北:九歌,1998),頁47。
[11] Tim Cresswell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2006),頁43。
[12] 陳芳明,〈反共文學的形成及其發展〉,《聯合文學》17:7 (2001.05),頁148-160。
[13] 相關資料,見中國文藝協會出版之《文協十年》活動手冊。本段為研究者採訪當年中國文藝協會作家王牌(王志濂)之口述紀錄,王先在回憶當年協會的盛況與會員眾多的情形。

【專論】居食城南:多元族群與多重歷史脈源的常民生活空間
臺北自清代以來的市街發展模式,即高度仰賴經濟基礎,區域的發展因商業活動的充裕,漸漸累積多元的人文活動風貌。從大臺北市街發展的脈絡來看,城南的拓墾與市街規劃,都與臺北都市幅員的擴張、居民族群多元的特色…

動盪時代的城南安居:外省族群流遷台灣的歇腳之地
戰後外省籍人士的遷徙,是一個漫長、輾轉而艱辛困頓的歷史過程。日本戰敗後,在台灣留下的房舍、事業及物品,原則上需依「臺灣省接收日人財產處理準則」接收,並由日產處理委員會統籌處理,進行轉撥各機關,或辦理標售…

多元族群的重組、衝突與融合
戰後的政治情勢,使兩岸人民皆無可遁逃地經歷了大時代的劇變,不論是外省人面臨骨肉相隔、流離失所的國仇家恨;或是本省人的認同困頓與迷惘、在語言和文化的錯位中拼湊支離破碎的國族想像…

城南的商業飲食文化與族群變遷
日治時期,由於領臺初期官吏士兵紛傳水土不服,使得總督很快的便注意到臺北蔬菜產量的匱乏,因而建立了種植日本蔬菜的獎勵制度,並總督府在南門外購地設置苗圃。城南一帶或因尚未開墾的田地甚廣,由少數住戶嘗試種植…

城南客:多元族群與信仰
城南的南昌路,日治時期即是兒玉町的主要街道,沿街商店林立,有自行車店、料理店、洋果子店、書店、洗衣店、理髮店、百貨行、碾米廠、木材行、雜貨店等,是城南經濟活動聚集的中心。商店主要由日本人經營,店家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