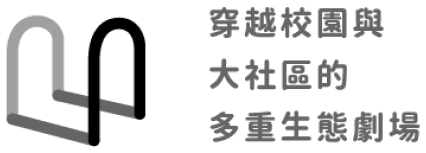植物園內:空間與人
路那
← 返回列表
植物園的空間規劃
在植物園中漫步,會發現園區內除了以植物學的系統來區分的多肉植物區、蕨類植物區外,也有著以生態系統區分的水生植物區,更有一些有趣的主題區,如民族植物區、植物名人園等。這麼多不同的規劃與分類方式,是如何形成的呢?
回溯台北苗圃時期,初建立的苗圃,係以種植的樹種來劃分區域。1904年,約有十多種分區,分別種植相思樹、柳杉、檜木、樟木、柳樹、柑橘、桑樹、紫檀、龍眼、雜木等等苗木。隨著苗圃購地擴張,1907年出現了占地一萬兩千坪的「樟苗圃」,約可養成苗木250萬株。隨著苗圃逐漸「公園化」,栽植苗木的比例下降了,觀賞花卉的比例則逐步攀升。此時的植物園,分為林業部、園藝部與母樹園三大區。其中,林業部有播種場四區、移植場七區;園藝部有見本園(觀賞園)三區、栽培區七區;母樹園則分為東西兩部分,各有21區與8區。
園藝部的見本園第一區,即今日的溫室花圃區。有大小型日蔭棚、中央儲水池與西側小池。北側有栽培園與防寒室,東側則有事務所。母樹園則在大池東側,在1912年購入原城南醫院的西側土地前,這片區域也常被拿來當成展覽會場地。
在1912年的購地後,今日植物園的規模便大抵成形。這片新加入的土地,後來一直維持草坪的狀態,展覽會便順理成章地移到此處舉辦。後來異地保存的欽差行臺之所以選擇此處,也是因其空曠的緣故。附近只簡單地栽種了一排亞歷山大椰子、大王椰子與露兜(林投)樹等熱帶植物,今日在和平西路入口處附近的棕櫚區,正是當年留下的印跡。
日治時期以植物分類為系統的規劃方式,在戰後縮小為9個區塊,在1963年,再依照郝欽松氏(Z. Hutchinson)分類系統,分為17區,分別展示裸子植物、木蘭科、樟科、番荔枝科、第倫桃科、豆科、殼斗科、薔薇科、桑科、山龍眼科、木麻黃科、楊柳科、蓮科、夾竹桃科……等等。1964年出版的《臺灣省林業試驗所植物園指南》中,記載了詳細的格局。儘管日後植物園多次想要改變分區,但植物不若動物,在「樹老根深」的情況下,難以簡單地說動就動。
無論如何,在1993年後,由於環境與生態教育理念的導入,植物園大幅地更動原先的十七分區。林試所生物系主任潘富俊為了讓植物園中的植物不再是知識分子的專屬,而是普羅大眾也能親近理解,援用了他在恆春熱帶植物園的經驗,規劃了「詩經植物區」、「民俗植物區」、「十二生肖植物區」等以趣味為主的園區。透過前期與後期的問卷調查,這樣的設置方式確實獲得了民眾的好評。然而另一方面,這樣的設置也存在著缺乏總體規劃,而流於主事者趣味的問題。對現任的園長范素瑋而言,她的任務之一,正是去思考「為什麼前人要把此物種在這裡?」透過這樣的考察,再去評估這些植物是否該繼續留在園區之內。在保留園區內既有的物種,去思考如何順應時空的變遷,為園區找到在歷史、既有脈絡與社會中的定位,才能使植物園能更加欣欣向榮。
常駐植物園:園丁、志工與警衛
呵護者
在講到植物園中的人物時,最常被提起的都是植物學家。然則,在植物學家之外,園丁也是維護植物園不可或缺的人物。
在植物園中,有一座神秘的「林火塗碑」,靜靜地坐落在林試所大樓前的綠蔭之中。這座由時任植物園負責人的金平亮三專門立碑紀念的林火塗,其生平迄今仍未有確切的考據,只知道他是臺籍雇員、在植物園工作近三十年不曾缺席,是個被評價為「發自內心喜愛植物」,而有著「現今臺北以至全島各地的行道樹與觀賞植物中,可能僅有極少數未經手於他」此般貢獻的認真員工,並在四十九歲時因病離世。
然而,我們真的不知道他是誰嗎?什麼樣的人才會經手大多數「臺北以至全島各地的行道樹與觀賞植物」呢?結合台北植物園最初成立時的名稱「苗圃」,答案或許呼之欲出──林火塗,應該是名園丁。也唯有園丁,才能以素樸的方式,讓植物學家感受到他對植物「發自內心」的喜愛。
在成立迄今超過120年的植物園,一向不乏熱愛植物的園丁身影。其中,更有父子兩代都是園丁的狀況──多虧了這些熱愛植物的園丁,才有如今蔚然成蔭的植物園風景。
傳遞者
植物的授粉,往往需要各式各樣的媒介才得以順利進行。同樣地,唯有透過植物園專家學者培訓過的志工,知識才能順利地傳遞到遊園者的耳內。
台北植物園的解說,約莫從1990年代左右才開始。在此之前,植物園的解說是定時定量的──每年植樹節的期間,由植物園專家們擔任解說者,舉辦數次親子活動。由於活動大受好評,因此要求加開場次的呼聲越來越高,然而植物園卻也面臨人力不足的處境。志工制度方才應運而生。
1992年,在市北師(今臺北市立大學)環教中心王佩蓮主任的協助下,植物園志工團招募了第一批志工。這些志工以國小教師占多數。由於此時期也是臺灣志工逐漸制度化並大力推廣的時期,加上教師原本便具有豐富的教學經驗,因此志工團慢慢地擴大。到了1996年正式成立「台北植物園生態保育志工服務團」時,已有90人的規模,也成了植物專家與普羅大眾之間最好的知識轉介者。
如今,植物園志工的服務範圍,早已不限於植物,還包括了古蹟與室內展館的支援。因此,目前的志工大抵分為假日解說組、平日解說組、腊葉館組、欽差行臺組和其他室內展館組等等。負責導覽的志工,大多在解說組,目前約有一百多人左右。令人驚訝的是,在這些志工中,有許多是超過七十歲的長輩!
守護者
儘管許多民眾將植物園視為公園,然而實際上植物園是有開園與閉園時間的,儘管不像動物園般會強制驅離閉園時間後仍在內逗留的人,但也絕非隨時晃進去都可以的公園。
為此,三班制的警衛,也就成了必備的存在。分成早、中、晚三班,24小時守護植物園的警衛,每班人數由1人到4人不等,一班需巡園4趟。連續工作6天,才休假2天。由於植物園的風景優美,因此這份工作乍看之下似乎相當愜意,然而攤開值勤時間與內容,卻絕不輕鬆。
舉例來說,植物園警衛的工作內容之一,是勸導遊客。不聽不知道,原來許多事情在動物園裡其實是不行的──比如做運動。此外,遊客形形色色,因此也出現了許多令人意想不到的違規舉動。舉例而言,為了拍到特定鳥類的照片,而瘋狂丟蟲吸引鳥兒過來取食的攝影客,也在勸導的範圍內。
由於負責處理的,是人的行為。因此,警衛們通常不僅深知園區內的動植物分布,腦中更有一份「植物園常客地圖」:固定前來拍攝的攝影迷、會帶動物前來放生的虔信人士、102歲超高齡的長輩與定時推輪椅帶長輩來此休憩的外籍看護等等,都在他們的腦海中的地圖上有著獨特的位置。如果說植物園是植物的博物館,那麼警衛們大概就是遊客的博物館了吧!
參考資料
李瑞宗,《台北植物園與欽差行臺的新透視》,臺北:南天書局,2007年。
〈來植物園當個快樂志工〉,https://kmweb.coa.gov.tw/subject/subject.php?id=27218&print=Y,2009.09.28撰,2021.05.28引用。
鄒欣寧,〈留給我們種子的人:臺灣植物園的植物學家們〉,「端傳媒」,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0815-culture-taipei-seeds-planning-2/,2019.08.16撰稿,2021.05.28引用。
張勵婉、徐露玉,〈樹木學不設限―潘富俊教授〉,《林業研究專訊》Vol. 27 No. 2,臺北:林試所,2020年。

【專論】植物之外:台北植物園
說到台北植物園,許多人腦海中跳出的第一印象,便是那一汪夏日時盛開的荷花了吧。植物園的荷花池,是今日臺北市頗為人所稱道的景點。然而這塊土地的歷史,實際上比我們所記得的還要淵遠流長──鄰近此地的三元街與西藏路,至清領時期尚是新店溪的支流。在水源無虞的狀況下,植物園一帶從史前開始,便是人群居住的地方。

植物園的奠基、擴張與縮減
台北植物園,前身係以栽培苗木為主的「台北苗圃」。台北苗圃的設置,出於殖民者對空間環境的美化需求,以及對林業開發的經濟需求等。1895年底,當日軍尚未平定全島時,總督府卻已在小南門外的官有地籌設苗圃。從中,不難看出日…

秘密植物,與植物園的秘密
台北苗圃/植物園(以下不分年代,皆稱植物園)建成後,在本土樹種的研究之外,影響最大的,便是熱帶植物的引進與栽培了。這也是為什麼日本領台後,在台北苗圃與恆春熱帶殖育場培養了各式各樣的椰子樹──大王椰子、亞…

遺跡、消失與現身:植物園內的建物們
在栽植苗木之外,植物園寬廣的園區,讓它成了各式公共建築舉辦活動的不二地點。自成立以來,此地便曾容納過醫院、動物園、古蹟、博覽會會場、神社、博物館群,甚至是廣播電台。這樣多元的面貌,使得植物園在孕育植物之外,似乎…

植物園內:空間與人
在植物園中漫步,會發現園區內除了以植物學的系統來區分的多肉植物區、蕨類植物區外,也有著以生態系統區分的水生植物區,更有一些有趣的主題區,如民族植物區、植物名人園等。這麼多不同的規劃與分類方式,是如何形成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