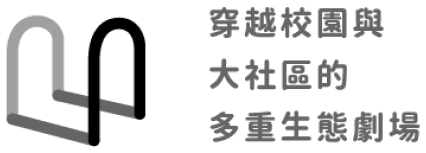【專論】植物之外:台北植物園
路那
早田文藏碑 by sunoochi
說到台北植物園,許多人腦海中跳出的第一印象,便是那一汪夏日時盛開的荷花了吧。植物園的荷花池,是今日臺北市頗為人所稱道的景點。然而這塊土地的歷史,實際上比我們所記得的還要淵遠流長──鄰近此地的三元街與西藏路,至清領時期尚是新店溪的支流。在水源無虞的狀況下,植物園一帶從史前開始,便是人群居住的地方。
史前人類的居所
歷史時代的居民們,是1901年首次知道這件事的。當時,透過佐藤傳藏的報導,此地發現「大加蚋堡貝塚」一事開始廣為人知。到了日治末期,人類學家金關丈夫與國分直一則在臺北第一中學(今建中)與今國語實小的範圍內發現史前遺址──事實上,國語實小的家長等候區中,便存在著一座考古槽呢!戰後,在1980年到1990年間,黃士強、劉益昌、劉鵠雄、郭素秋等學者陸續在此進行考古發掘,證實距今約4500年的新石器時代中期,就有人類在此活動。
令人訝異的是,人類自那時開始,便從未停止在此活動──距今4500年到3500年的一千年間,有「訊塘埔文化」;距今3500年到2100的1400年間,有「圓山文化」;距今2100年到1800年的300年間,有「植物園文化」;而距今1800年到500年間,則有著廣為人知的「十三行文化」。一個位置,竟然可挖掘到四種史前文化,即便在考古遺址中,也屬罕見。
以「植物園」命名的植物園文化興起時,古臺北湖的湖水面積正逐漸縮小,盆底逐漸露出。先民們為了適應環境,將原本以漁獵為主的生活方式改為旱作農業。除了植物園附近,植物園文化也分布在大漢溪西岸的樹林與新莊一帶,是臺北相當重要的史前文化。其在植物園一帶的分布範圍,以植物園為中心,北到南門國中,東至南海學園東側、西邊和南邊則以三元街一帶為界。
漢人到來之前

〈淡水與其附近村社暨雞籠島略圖〉,1654。圖中淺綠色方塊即為雷朗社所在地。
1624年,荷蘭人成為臺灣的統治者。出於統治與貿易的需求,30多年後的1654年,荷蘭人繪製了「淡水與其附近村社暨雞籠島略圖(Kaartje van Tamsuy en omleggende dorpen, zoo mede het eilandje Kelang)。這幅被臺灣史研究先驅曹永和評為「臺北盆地出現於古地圖較詳細者當以此圖為首次」的地圖,也詳細地記載了當時居住於臺北盆地的原住民聚落。當我們將目光投注到今日植物園一帶時,會發現此地被稱為「Rieuwwerowar」,今譯雷朗(又稱了阿、老匣、龍匣、荖厘)。那即是最早對此地居民的紀錄了。根據臺灣史學者翁佳音的考證,此地大約有三十幾戶人家,共一百多人的聚落。此地在清領時期之所以稱為「龍匣口庄」,在戰後又有多個里以「龍」為首字,其實都源於墾殖的漢人將「Rieuwwerowar」以閩南語音譯為「龍匣」而來。所謂的「龍匣口」,即意指「龍匣社的入口」。
居住在龍匣一地的,自然便是凱達格蘭族的原住民了。實際上,以臺北、宜蘭為分布地的凱達格蘭族,還可細分為巴賽族(Basay)與雷朗族(Luilang)。居住在植物園一帶的,即是雷朗族原住民。他們和居住於上下游的雙園、永和、秀朗等三社合稱為「雷朗四社」。在漢人到來之前,他們習慣住在往下挖三尺的木屋之中,飲食則以魚、鹿和耕作的薯芋為主食。如果有客人來,會以雞和冬瓜為客人加菜。然而,隨著漢人墾殖的入侵,整個凱達格蘭族都慢慢地步向了漢化的命運。到了18世紀後,漢人已成此地的優勢族群,原住民族過往的魚獵農耕生活,至此再不復見。一同消失的,還有在平原上奔跑的梅花鹿。
最早到此地開墾的漢人,為蘇氏、連氏與武功周氏,又以末者最為著名。目前所知最早的墾戶為周賢明,時間約在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周賢明在取得了大加蚋三板橋的墾權後,在族人周廷部的協助下往南開墾。在此波開墾潮中,周廷部獲利甚豐,被稱為「周百萬」。隨著漢人的開墾,國語實小與植物園一帶也築起了許多墳墓。先前提及的周氏家族,其宗祠即設立於古亭庄一帶(今和平西路一段63號)。
從苗圃到植物園:栽培苗木與深入研究
1895年,臺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對於新附之地,眾多殖民者摩拳擦掌,立志要在此實踐自己的理想。為此,首要之務是仔細地調查臺灣的一切。其中,臺灣的山林更是不可錯過的寶庫。總督府邀請了眾多學者前來勘查,最後得出了除了砍伐已知的林木外,對於整體的林木也應該有更多理解的結論。加上初入臺北城的殖民者,發現清領的街道竟是「禿山草野相連」,除了人民居住的村落外必然會種植竹子做為防衛外,沒有特別種植樹木的習慣,對此大表驚訝。植物學者田代安定在他的《臺灣行道樹及市村植樹要鑑》中,寫下他認為城市中的行道樹是「社會的裝飾物」,反映出一國「文明」與「進步」的格調。
既然行道樹是反映文明與格調的重要裝飾,那麼作為日本首個海外殖民地,臺灣的行道樹自然不可馬虎。
苗圃的籌設,係由「民政局殖產部林務課」負責。此單位設置於1895年中,被公認為日本領臺後最早專責「林政」與「森林調查」的機關單位。林務課的首要任務,即理清林野產權、處理樟腦專賣事業、進行林業基礎研究與實驗等。為了達成最後一項任務,林務課遂決定在臺灣北部的臺北與南部的恆春,各設立一實驗場所,那便是「(臺北)苗圃」與「恆春熱帶殖育場」設立的根源了。
恆春熱帶殖育場的設立,背後的推手乃是植物學家暨人類學家田代安定。至於台北苗圃的設置,據田代安定的回憶,乃是當時在殖產局擔任部長的橋口文藏提出的。被森鷗外評價為「大膽之人」的橋口文藏,到臺灣前曾至墨西哥探險。1896年,橋口接掌臺北縣知事,負責今日北北基宜的行政事務。
-768x560.jpg)
民政部殖產局苗圃(約1905年)(台北植物園典藏)
橋口認為,苗圃的設立,其目的有五:第一,研究本島樹木;第二,試驗國內外樹木栽培情況;第三,養成樹苗;第四,作為全島苗圃示範點;第五,使人民理解造林的必要。於是,1895年底,「苗圃」正式在小南門外的陸軍衛戌病院(今和平醫院院址)旁的官有地成立。
然而,這不代表「苗圃」往後就一帆風順。相反地,由於衛戌病院即將擴建,它反而得流落四方。對需要土壤培育的植物來說,這無疑不是一個好的生長環境。為了不使苗木居無定所,田代安定撰寫了〈總督府殖產課苗圃整理上意見書〉、〈中央苗圃組織改正案〉等一系列建議提案。然而他的意見並未被採納,這也成了他日後前往恆春成立熱帶植物殖育場的理由之一。儘管如此,這些觀點,確然地影響了日後苗圃的試驗事業與方向。
1900年,苗圃終於在小南門外覓得較舊苗圃更適當的土地。此時種植的植物,被分為「母樹園」、「果樹園」、「花卉園」三類。隨後,便是逐步地購地擴建,終究在1905年形成了我們今日熟悉的植物園範疇,也逐步整建為我們熟悉的今貌。此外,經過數年的推廣後,苗木的栽植已成為時人的愛好,在不乏市民前來購買苗木的狀況下,整建後的苗圃也逐漸成了市民休憩時頗為熱愛的場地。
在提供市民休憩場地之外,苗圃亦是臺灣林業教育之濫觴。第一回林業講習,即在此地舉辦。1908年,隨著總督府園藝試驗場的成立,台北苗圃也停止了果樹的栽培,轉而更加致力於栽種外來的觀賞植物,因此愈發獲得市民的關注。
1911年,時任林業試驗場主任的金平亮三,在《臺灣日日新報》一篇〈誤植的樹木〉的報導中,提到他認為苗圃當時以外來觀賞植物為栽種要點的方向是錯誤的,應該要致力於培植本土植物才對。這使得台北苗圃逐漸脫離單純地栽培苗木,而往兼具學術研究與教育功能的「植物園」邁進。
金平亮三的觀點,儘管不乏殖民利益的考量,然而更多的是對本地植物的研究興趣使然。按歷史學家吳明勇的分析,殖民政府對臺灣山林與植物的研究,可概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係以有「日本植物學之父」美名的牧野富太郎為首,在川上瀧彌與早田文藏等人的時代達到高峰。此一階段的研究人員,多是隨軍隊而來的東京帝大教職員。他們是明治維新後第一批接受西方教育的日本科學家,來到臺灣後,震撼於臺灣豐饒的蘊藏,因此力勸總督府進行深度調查,而不只是掠奪式的經營。1919年,研究的核心轉移到林業試驗場。在此階段,植物園開始成了重要的教學與研究場域。代表人物包括佐佐木舜一、金平亮三、山平由松等人。1928年,臺灣帝國大學(今臺灣大學)成立後,調查重心隨之轉移。吳明勇認為,在這三階段中,以林試場時期的研究最有系統,且成果質量並重。
一邊研究,一邊推廣苗木的台北植物園,在明治年間每年培養約16萬株苗木。其中約有六萬是由民間單位購買,餘者則撥給公家機關使用。當時,植物園中培育的樹種包括了相思樹、樟樹、榕樹、金露花、七里香、樹蘭等。其中,金露花與樹蘭至今還是公園、人行道乃至於安全島上常見的植物。

金露花(Forest and Kim Starr 攝)

樹蘭(songshowlin 攝)
不只是種植物的地方:公園、設施與活動
栽植苗木之外,苗圃寬廣的園區,亦是置入各式建築與舉辦各類活動的絕佳地點。最早遷入的園外建築,是1903年的臺北避病院(當時的傳染病隔離所)。它的地點,即位於欽差行臺往北約百公尺處。臺北避病院後來改名為「城南醫院」,直到1913年7月遷至大龍峒町,才又更名為「稻江醫院」。
在建築之外,苗圃也是舉辦活動的好地方。1908年後,台北苗圃分為林業部、園藝部、母樹園等三大塊。其中,位於「鴨池」(今荷花池)東側的母樹園,由於是在1905年才購入的土地,種植的樹苗尚小,因此相對空曠,也就成了舉辦活動的好地方。
1910年,民政長官大島正滿的退休送別會即在此舉辦,自此開啟了台北苗圃與大型活動的緣分。然而,在苗圃舉辦的所有活動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過於1916年舉辦的臺灣勸業共進會,與1925年舉辦的始政三十年臺灣博覽會。

臺灣勸業共進會第二會場迎賓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
1916年舉辦的臺灣勸業共進會,係以「提倡實業、獎勵產業」為主題,共有兩個會場。第一會場在距離不遠的總督府新廳舍建設地,第二會場即設在苗圃。為了這場展覽會,官方還新建了「迎賓館」(即日後的「商品陳列館」)。戰後此地轉為國立歷史博物館,可惜原建築在1971年遭到拆除。如今屹立在荷花池旁雄偉的中國北方宮殿式建築,即是「迎賓館」的原址。
除了迎賓館外,台北苗圃另外在園區內設置了「番俗館」、「南方館」、「演藝館」、「奏樂堂」等館舍,並在展覽會的後期,舉辦了夜間大園遊會。據統計,到苗圃觀展的人次有28萬、全體展覽人次則有80萬之多,完全超出主辦單位的估計──根據1905的調查,直屬臺北廳的人口,也才7萬4千多人。即使隨著臺北的都市化而導致人口暴增,到1920年代的調查,臺北人口也差不多只有16萬人左右。從這個數字,不難看出此次展覽的成功。來參觀的人,顯然並非只有臺北市民而已。
除了熱鬧的博覽會,苗圃一度也成了動物園的預定地。1913年,「博物館附屬動物園」在苗圃內成立。兩年後,動物們再度搬家到圓山,才成了大家熟悉的「圓山動物園」。
「討番凱旋祝賀會,九月五日在台北苗圃舉辦」〈伊能嘉矩手稿〉,1914年,臺大圖書館典藏
植物園也是殖民者誇耀己身勝利的重要場所。日本領臺初期,無論原漢,都有武裝集結抗日的活動。而日本政府對原住民初期更是以武裝鎮壓為主。因此,在1913年到1914年間,苗圃就舉辦了兩次「討蕃凱旋祝賀會」──殖民政府對林木的掌控需求,是在治理全境之外,對原住民征討的又一重理由。植物園在此成了殖民者誇耀己身勝利,與「馴服」臺灣植物的象徵。因而,當1923年裕仁皇太子來到臺灣時,他也到此處參觀當時舉辦的「生產品博覽會」。
1925年,是日本統治臺灣屆滿30周年。因此而舉辦的「始政三十年臺灣博覽會」,其目的在於對臺灣本島、日本內地與國外列強等展示殖民統治的成功。然則,由於1923年發生關東大地震,加上此時期正逢景氣低迷,因此不若十年後的「始政四十年」博覽會要來的聲勢浩大。儘管如此,原訂展出十天的博覽會,因迴響踴躍,還是順延了數日不等。此一博覽會的會場包括新公園博物館、植物園、總督府舊廳舍與專賣館四處。其中,身為第二展覽會場的植物園,係以商品陳列館為中心,展出臺灣與日本的產品。為此,主辦單位在商品陳列館周遭新建了林產館、地方館、臺灣即賣館、內地即賣館與演武館等展覽館,並開放植物園的空間給自營商與飲食店進駐。此外,入口也新建了附有燈飾的裝飾門,以供民眾夜間參觀。值得一提的是,參加本次展覽會的自營商中,有以臺灣料理聞名的江山樓。據史料紀載,江山樓租下五十坪的臺灣料理展示場,並提供價廉物美的臺灣料理。其人推廣臺灣料理的熱切由此亦可窺見。
1921年,台北苗圃正式改稱台北植物園。三年後,中央研究所林業部腊葉標本館落成了。這棟建築,象徵了台北植物園不單單是孕育苗木的「苗圃」,也不只是栽培園藝植物或本土植物的花園,更是學術研究的重鎮。腊葉館落成後,植物學者佐佐木舜一(1888-1961)即在此研究臺灣植物。他最知名的成就,即為替臺灣植披建立系統帶狀分類,制定高山植物帶的高度界線。

腊葉館(寺人孟子攝)
在腊葉館門前的水池旁,豎立著早田文藏紀念碑。有「臺灣植物界奠基之父」美譽的早田文藏,對辨識與分類臺灣植物有著莫大的貢獻。有意思的是,被後人建碑紀念的早田文藏,本身也替另一位植物採集先驅佛里神父(Père Urbain Jean Faurie,1847-1915)在植物園的林業試驗場辦公室前立了半身像。隸屬於巴黎外方會的佛里神父,為了宣教前往日本。他籌措教會費用的方式,便是製作並販售植物標本。1903到1915年間,佛里神父兩度來臺採集植物標本。不僅早田文藏的研究有賴佛里標本才得以開創,他的標本也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歐洲植物學家了解臺灣、日本、韓國與夏威夷植物的重要資源。標本採集者與植物學家攜手同行,打造出臺灣植物的認知體系。
儘管對臺灣植物學有著舉足輕重的貢獻,然而無論是佛里神父紀念碑,抑或早田文藏紀念碑,在戰後都遭到無情的毀棄。值得慶幸的是,在戰後七十年的今日,二碑已復原至原來的位置。雕像的復位,除了表彰人物的功勞外,更令遊覽者因而得以具像化地理解臺灣植物分類的歷史。
除了對臺灣植物的研究外,台北植物園也派遣了許多專家前往國外。據植物園所稱,到了1930年時,園內已有千餘種植物,過半係由國外引入。
在保存國內外植物之餘,植物園也保存著過往的記憶。1932年,原來矗立於今中山堂一帶的欽差行臺,經一場保存與否的激辯後,決議將建築部分主體移置植物園內。在清領時期興建的欽差行臺,在日本領臺的初期則成了總督府舊廳舍。戰後,此地一度成為公家宿舍與林業陳列館。掩映在大王椰子樹後的欽差行臺,背後是一段不應被遺忘的歷史。
戰後的植物園:南海學園的進駐
1945年5月31日,美軍針對島都臺北進行空襲。被稱為「臺北大空襲」的這場轟炸,讓臺北滿目瘡痍。這段血淚斑斑的歷史,如今唯有在植物園中的大王椰子身上可追憶。那坑坑巴巴的正是四處彈射的彈片造成。
甲午之戰,讓日本人得以統領臺灣。二次世界大戰,同樣地讓他們不得不離去。隨著日本帝國舉手投降,國民政府前來接收,植物園邁向了下一個階段。
令人驚訝的是,此時期的史料可謂既稀少又殘缺。據曾任台北植物園園長的董景生所言,「很多1940、50年代的資料都找不齊,我們需要更多史料來解讀當時歷史」,有待更多研究者積極投入。
目前所知者,為1945年10月,森林學家林渭訪(1896年-1974年)應行政長官公署長官陳儀之邀,來臺接收林業試驗所,為戰後首任所長,直到1965年退休。當時,留用了一些日本時期的研究者,大名鼎鼎的田代安定也在其中。至於園長,應是由廣州中山大學派至臺灣考察,後應林渭訪之邀擔任園長的植物分類學家蔣英。由於蔣英日後回到中國,在臺灣被視為「附匪分子」,資料或許因此難以尋覓。然而,根據中國留下的蔣英資料,他在臺期間,整理了約三千件標本與一千六百多張標本照片攜回中山大學植物研究所,同時發表《考察臺灣植物簡報》一文。然而蔣英的任期至何時為止?他在臺灣待了多久?繼任者是誰?這些都有待更進一步的考察。
戰後,植物園內原先富有日本官方色彩的建築,在去除殖民色彩的考量下,進行了館舍的再利用。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後,在教育與文化上採取了「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的方針。其中一項極為重要的,便是在臺灣推行大約於1932年標準化的、新「國語」,以「教化」當時說母語與日語為主的臺灣人。為此,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進駐了由井手薰設計、於1928建造完成的建功神社。為了推行國語而發行的《國語日報》也在此發行。鄰近的「國語實小」乃至於後來的「國語日報社」等,自然也與此一脈絡息息相關。除了國語日報外,接收了「臺灣映畫協會」和「臺灣報導寫真協會」後成立的「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臺灣電影攝製場」,亦在1946年遷入植物園。
1950年代,植物園迎來了另一個大變革,那便是「南海學園」的誕生。1949年國民政府撤退來臺後,在蔣中正指示下,時任教育部長的張其昀(1901-1985),便參照了西方博物館群的概念,試圖將社會教育與公園結合,「計畫在臺北市區和郊外,建立兩個文化中心」以成為「中國文藝復興必須的礎石」。市區的文化中心,即是植物園東側原武德會用地、建功神社與商品陳列館。除了改變建物的原有功能外,外在的形式也必須再改造,藉以形塑「中華正統」的國族氛圍。在此規畫下,「南海學園」成立了:由中央圖書館、國立臺灣藝術館、國立歷史博物館、國立教育資料館、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與國立教育廣播電臺、孔孟學會等單位組成。

過去的建功神社搖身變為南海書院(CartoDD897 攝)
儘管這些館舍都找來了當時知名的建築師修築或翻新,然而在缺乏總體規劃下,南海學園與鄰近的植物園,總是有著微妙的隔閡感──明明近在咫尺,卻像是油和水一樣,彼此毫不相容。在商品陳列館時代仍能融入植物園的建築量體,在史博館時代卻因入口位置改變、模仿紫禁城等原因,只留給植物園一片背影的紅牆。此外,在南海學園中缺乏與植物有關的景觀設計,也微妙地凸顯出兩者間毫不相關的意味。
南海學園的設立,見證了臺灣戒嚴時期為了「自由中國」的法理性,以及在此思考下,為了對抗中國文化大革命而發起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之痕跡。作為戰後重要的展覽園區,南海學園亦存放著數代臺灣學子的青春回憶。然而另一方面,植物園的面積,因需容納南海學園的設置,無疑縮減了許多。
令人遺憾的是,南海學園日後因空間不足,館舍紛紛外移。加上建物與土地各有歸屬、狀態複雜等因素,逐漸地淡出臺北人的生活之中。儘管曾有「大南海計畫」等針對館舍群再利用的思考,然而迄今卻缺乏一整體而可行的計畫。
綜觀植物園自日治成立以來,其存在便持續地受到政策的影響,而從原先的母樹園,改變為兼容植物研究與展示,帶有公園性質的「植物園」。其後,更曾多次舉辦各式博覽會、祝賀會、慶賀會乃至於動物園等與植物園的「本業」不甚相關的活動。日治後期興建的武德殿與戰後的南海學園等官方建築,乃至於林近豪宅的購地爭議,亦不斷地展示了政策的力量如何可以輕易地改變地景。因此,當我們今日漫步於植物園中,享受都會裡難得的綠意與寧靜,並從中學習植物知識與觀賞生態之美時,或許也該意識到這份寧靜與美並非永存不變,而是需要許多人的細心呵護與大聲捍衛才得以持續存在。如今的植物園,正是前人留給我們的遺產。如今的我們,又想要留下什麼樣的植物園給後人呢?在捷運萬大線即將開通的今日,植物園與南海學園的議題或許又將重現。你心目中理想的當代植物園樣貌,又是什麼呢?
參考資料
專書
楊仁江,《臺灣布政使司衙門之調查研究與修護計畫》,臺北:臺北市政府,1991年。
李瑞宗,《台北植物園與欽差行臺的新透視》,臺北:南天書局,2007年。
王鴻裕等編纂,《萬華區區志》,臺北:萬華區公所,2009年。
論文
林品章,〈日治時期始政三十年紀念展覽會之研究〉,臺北:臺科大設計研究所碩論,2003年。
留方萍,〈一個聚落的生與死──三重市後埔仔的聚落發展與地方感形塑〉高雄:高師範地理所碩士論文,2006年。
吳明勇,〈近代臺灣林學實驗起源地臺北「苗圃」之建立與經營〉,《臺北文獻》第164 期,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08年6月。
魏可欣,〈近代化進程中建功神社的容顏與活動〉,《國立歷史博物館學報》,臺北:史博館,2016年12月。
卓克華、王啟明,〈台北植物園臘葉館的創建暨沿革考〉,《臺北文獻》第196 期,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16年6月。
網路資料
林翠儀,〈臺灣桂竹與日本植物學之父牧野富太郎〉,https://www.nippon.com/hk/japan-topics/g00779/?pnum=4,20210523瀏覽。
廖靜慧,〈1895之後 那些讓臺灣植物躍上國際舞臺的日本科學家們〉,https://e-info.org.tw/node/207642,20210523瀏覽。
農傳媒,〈【攝影展】台北植物園老照片徵集展〉,https://www.agriharvest.tw/archives/28692,20210523瀏覽。
〈佐佐木舜一〉,https://sites.google.com/site/ur8335/22-2,20210523瀏覽。
潘子祁,〈植物園120歲發聲 我是博物館不是運動公園〉,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81408/,20210523瀏覽。
〈山本由松〉,https://sites.google.com/site/ur8335/%E5%B1%B1%E6%9C%AC%E7%94%B1%E6%9D%BE,20210523瀏覽。
林小昇,〈稻江醫院〉,「林小昇之米克斯拼盤」,http://linchunsheng.blogspot.com/2011/08/blog-post_31.html,20210525瀏覽
莊永明,〈圓山動物園開場〉,「莊永明書坊」,http://jaungyoungming-club.blogspot.com/2015/04/blog-post_20.html,20210525瀏覽。

【專論】植物之外:台北植物園
說到台北植物園,許多人腦海中跳出的第一印象,便是那一汪夏日時盛開的荷花了吧。植物園的荷花池,是今日臺北市頗為人所稱道的景點。然而這塊土地的歷史,實際上比我們所記得的還要淵遠流長──鄰近此地的三元街與西藏路,至清領時期尚是新店溪的支流。在水源無虞的狀況下,植物園一帶從史前開始,便是人群居住的地方。

植物園的奠基、擴張與縮減
台北植物園,前身係以栽培苗木為主的「台北苗圃」。台北苗圃的設置,出於殖民者對空間環境的美化需求,以及對林業開發的經濟需求等。1895年底,當日軍尚未平定全島時,總督府卻已在小南門外的官有地籌設苗圃。從中,不難看出日…

秘密植物,與植物園的秘密
台北苗圃/植物園(以下不分年代,皆稱植物園)建成後,在本土樹種的研究之外,影響最大的,便是熱帶植物的引進與栽培了。這也是為什麼日本領台後,在台北苗圃與恆春熱帶殖育場培養了各式各樣的椰子樹──大王椰子、亞…

遺跡、消失與現身:植物園內的建物們
在栽植苗木之外,植物園寬廣的園區,讓它成了各式公共建築舉辦活動的不二地點。自成立以來,此地便曾容納過醫院、動物園、古蹟、博覽會會場、神社、博物館群,甚至是廣播電台。這樣多元的面貌,使得植物園在孕育植物之外,似乎…

植物園內:空間與人
在植物園中漫步,會發現園區內除了以植物學的系統來區分的多肉植物區、蕨類植物區外,也有著以生態系統區分的水生植物區,更有一些有趣的主題區,如民族植物區、植物名人園等。這麼多不同的規劃與分類方式,是如何形成的呢?